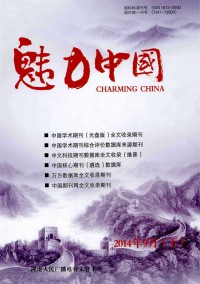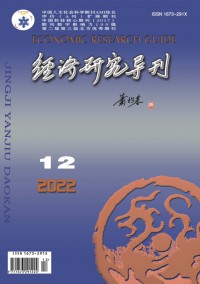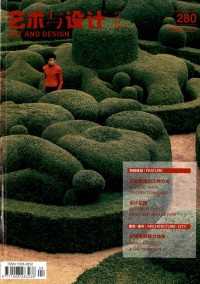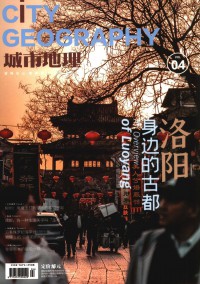城市公共行政論文匯總十篇
時間:2023-03-20 16:08:06
序論:好文章的創作是一個不斷探索和完善的過程,我們為您推薦十篇城市公共行政論文范例,希望它們能助您一臂之力,提升您的閱讀品質,帶來更深刻的閱讀感受。

篇(1)
一、角色的錯位
1.最高法院關于刑事訴訟法的司法解釋第一百七十六條第二款規定:“起訴指控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指控的罪名與法院審理認定的罪名不一致的,仍應當作出有罪判決。”而事實上,法官的職責中并沒有提起公訴的權利,對指控的罪名只能有認定成立或不成立的二元論,根本不存在法官認定與控訴方指控罪名不一致的情況,但在司法實踐中,改變定性時有發生,法官充當了控方的角色,使得控辯雙方的對抗成了控審與辯方的搏擊。
2.最高法院等六機關1998年1月19日公布的《關于刑事訴訟法實施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三十八條的規定,對于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公訴案件,無論人民檢察院是否派員出庭,都應當向人民法院移送全部卷宗和證據材料。法官在庭審前對移送的材料進行梳理、歸納、確認,并對重點部分進行圈點,以便庭審的順利進行。不覺中站在控方的立場上看待問題,先入為主,使得案件的庭審流于形式。
3.美國律師界有句名言“最好的辯護就是主動進攻”,事實上,律師在現實中有種種顧慮,“不善于”、“不愿意”、“不敢于”與公訴方進行激烈的對抗。面對強大的公訴力量,辯護律師為了維護當事人的最低利益,很少作無罪辯護(即使無罪成立,控方也絕不放過抗訴的機會),“往往不得不從有罪的角度作從輕辯護,引導法庭確立另一項相對較輕的罪名和法定刑,實際上演變成對當事人的變相指控”。
二、控辯力量失衡
修訂后的刑事訴訟法最大的貢獻是法官從對被告人進行積極追訴的角度轉變為居中裁判、主持正義的消極角色,吸收了英美法系的當事人主義,無疑是訴訟法學的一大進步。而實踐卻與立法精神背道而馳,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1.辯護律師提前介入的作用未能體現。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四條至第一百二十七條的規定,偵查機關羈押犯罪嫌疑人的期限可達7個月之多,甚至更長,偵查機關利用國家賦予的強制措施,收集了大量的證據,檢察官依照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條的規定,已獲得公安機關移送的主要證據。而刑事訴訟法第九十六條第一款規定,律師在偵查階段只能提供法律咨詢,并未規定律師可以調查取證,律師沒有權利知悉案件的任何證據,只能在案件移送起訴后才能調查取證,律師輸在起跑線上已成定局。律師在偵查階段不能調查、閱卷,使得律師提前介入成為走過場,對改變犯罪嫌疑人的地位作用甚小。
2.層層設防。(1)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律師在查閱、摘抄、復印相關證據范圍由檢察院確定,檢察院移送的證據材料往往是部分證據的復印件,使得一些有價值的材料與律師擦肩而過,先天不足的律師難以在激烈的法庭辯論中有所作為,只能在初犯、偶犯、認罪態度等無關痛癢的酌定情節上為被告人爭取。(2)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七條第二款規定,辯護律師經人民檢察院或人民法院許可并且經被告人或者其近親屬、被害人提供的證人同意,可以向他們收集與本案有關的材料,無疑讓缺少司法救濟(強制措施)的律師雪上加霜。證人作證對國家是義務,而對辯護律師卻是權利,許多有價值的證據因被害人或其證人的不配合而滅失(有些案件如殺人案件,如果積極配合,豈不有助紂為虐之嫌),使律師的努力付諸東流。(3)人力與經濟的懸殊。我國刑事訴訟法明文規定,被告人最多只能聘請兩名律師,而對檢察院辦案人員卻沒有相應的限制,甚至全院出動也在所不惜。由于種種立法及現實的限制,使得律師付出的艱苦的勞動難以得到成正比例的回報,浪費了本來就有限的律師資源,被告人的經濟實力也成為辯護律師是否能有效辯護(取證)的重要影響因素。
為保護國家和廣大人民的安全,維持良好的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而有效的控制犯罪已得到普遍的重視,而在刑事訴訟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權利卻未得到足夠的關心。要實現社會的“權力本位”向社會的“權利本位”過渡,通過刑事訴訟法程序公正而獲得實體的真正公正,就必須徹底清除封建思想及法律心理意識對刑事訴訟的影響,從立法和司法實踐中尊重被告人的人權,切實的維護辯護律師的合法利益,筆者從以下幾個方面提出解決措施:
一、建立均衡對抗制
“司法權一旦與沖突的一方具有某種價值取向和利益性的偏異傾向,就會使人對裁判的公正性產生懷疑,因此法官在訴訟中必須保持中立,對控辯雙方主張的利益給予同樣的關注,在訴訟中只能根據雙方提供的證據去判斷‘是與非’,而不能身體力行去證明沖突一方的‘是與非’,嚴禁法官先入為主,對沖突一方產生偏見”。因此建立均衡對抗制,法官居中裁判意義重大。
1.取消控方開庭前移送證據或者全部卷宗的做法,實行英美法系的“訴訟一本主義”,即“只能向有管轄權的法院提出具有法定格式的起訴書,而不得載入可能使法官對案件產生預斷的文書和證物”。實際操作中,只需提供起訴書及證人名單即可,從源頭上防止先入為主情況的發生。
2.建議律師介入調查取證的時間提前,即在犯罪嫌疑人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采取措施之日起即可介入調查并參與當事人的活動,取消對律師調查取證權的不合理限制。
3.程序公正集中體現在權利的分配上,因此必須建立理性的舉證分配制度,給控辯雙方平等的調查取證權。
二、刑事訴訟證據制度的構建與完善
證據是訴訟的核心,是事實的再現的載體;訴訟是證據的搏擊,使證據的價值得以界定。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刑事訴訟證據制度的滯后弊端日趨明顯,以合法性、維護人權為視角,建立與時代合拍的證據制度迫在眉睫。在此,美國在證據規則方面的“毒樹之果”原則值得借鑒。(“毒樹之果”原則在國內的很多著作中均有介紹,不在論述。)但切不可全盤照搬,或簡單的加以否定。我們應當順應民主的潮流,在對法律文化傳統和民族心理差別分析的基礎上,吸收美國“毒樹之果”原則的精華,“在懲罰犯罪和保障人權中找到平衡的支點”。
三、廢除“可以派員”的規定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九十六條的規定,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偵查機關“可以派員”參加。在現實中“可以派員”變成“經常派員”,在被監督的情況下,犯罪嫌疑人如實向辯護人陳述案情存有顧慮,無法按照真實的意愿向律師供述有關事實,也無法就辯護事由與律師協商,對律師工作開展影響是不言而喻的。